
当地时间7月21日傍晚,快抵达坦桑尼亚的海岸时,刘勇挥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。受访者供图
今年6月30日,刘勇在印度洋的海面上吃了一块巧克力——这是他收到的56岁生日礼物。他对着大海和星空许愿,第一希望世界和平,第二希望顺利抵达终点。
当时,这名探险家已经在海上漂了45天。此前,他和另外3名队友,驾驶一艘长8米的无动力小船,仅靠人力划桨,挑战从东到西横渡印度洋。这是他的冒险,也是他的科研。
正值南半球冬季对探险者最“友善”的时间窗口,一群英国人比刘勇他们早2.5天出发——无论谁先抵达,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无后援、无动力划船横渡印度洋的团队。
两年前,刘勇还曾以同样的方式横渡大西洋。如果印度洋之行顺利,他会是首位划桨横渡两大洋的亚洲人。
船上的日常是,两人一组划船两小时、休息,换另一组划。刘勇的3名队友来自欧洲,分别是银行家、护士和网络工程师。除了必要的交流,他们很少谈及自己的生活。即使说话,人的声音也很容易淹没在海浪与海风的双重呼啸中。
出发几十天后,刘勇身上几乎找不到一处完好的皮肤了,坐在船上划桨时,他感觉浑身被烙铁灼烧,靠止疼药缓解疼痛。
不在冒险路上时,刘勇是四川旅游学院山地旅游研究院院长。这名教授每个学期最少要给本科生授课32课时,要带着研究生去四川山区做田野调查,还主导了一个专注山地旅游的科研团队。他发表的专著、译著、高水平论文超过200万字,手头上还有好几个科研课题正在进行。
抓着桨在印度洋上划船时,刘勇也抓着工作进度。他利用卫星通信,参加了两次科研例会,远程盯着学生的论文。他团队里有3名研究生刚刚成功申请赴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,他在小船上表达了喜悦与祝福。
刘勇的一名研究生王金鹏记得,导师在印度洋上参加科研例会时,镜头中的他随着海浪的起伏摇晃。王金鹏觉得导师老了很多,声音发哑,胡子、头发都白了,和平常学校里穿着POLO衫、戴着金属边框眼镜的那个“绅士”很不同。
每隔一段时间,刘勇会收到学生确认他平安的信息,也收到他们的科研进度汇报。四川旅游学院教师李婷婷回忆,有一次,刘勇“消失”了5天,他的同事、学生互相打听情况。后来,刘勇出现了,他回复说因为连日阴天,船上的太阳能板充电不足,网络连接失去能源供给。
这艘小船挑战的是印度洋最长的航线,从澳大利亚西岸的卡那封出发,沿途没有海运、航空航线,没有前人经验,也没有后援,“几乎是没有任何心理依托的”。从气象卫星拍下的图片上看,洋流像打结的绳索,缠绕着超8000公里的航线,强风能卷起8米高的海浪。刘勇说,他一度被巨浪卷入深海里,靠着安全绳重新爬回船舱。
即便是风平浪静的时候,身高1.88米的刘勇和另一位队友挤在两米长的船舱里,也很不舒服。他回忆,海水会不断涌进船舱,打湿睡袋、衣物,人很难翻身,脚总是得蜷缩着。海水泡透了他的身躯,连挪动屁股都特别疼。
他们用GPS(全球卫星定位系统)和罗盘导航,用制水机把海水转化成淡水。在各种户外脱水食品中,他只喜欢咖喱鸡饭。上船的第一个月,刘勇晕船严重,一度边划船边呕吐。大浪把船桨弹回来,打在他的腿上、手上。

刘勇(左一)带学生在野外调研。受访者供图
“依靠人力划桨,抵抗不了洋流。”刘勇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,他一度濒临绝望,有种“死不了,却又到不了岸”的感觉。
刘勇挑战的印度洋,特有的生态风貌加重了他的孤独感。他对学生描述,两年前,他划过大西洋,沿途看到许多海洋动物,海里有鱼,天上有鸟,不会觉得很单调,但在印度洋上他偶尔才看到鱼。曾有一个月的航程,他发现周围上千公里内都没有小岛,甚至很多时候天空中也看不到鸟。
他说,横渡大西洋就像在看得见光亮出口的隧道里开车,印度洋上则充满了未知,看不到有光的出口。
刘勇通过处理眼前的麻烦缓解情绪,比如,他认真修理被海浪拍坏的制水机,包扎身上的伤口。“平常不懂得珍惜的小事,在那会儿懂得珍惜了,比如喝一杯干净的水。”
他用大段大段的时间与自己对话。刘勇说,自己爱上探险,也是迷上了在自然环境中独处的感觉。
他在海上想清楚了,平时参评荣誉奖项需要花时间准备申报资料,可那些“称号”不能说明个人研究水平,耗费许多精力填表、汇报,可以舍弃;能研究的学术方向那么多,要花时间在真正的兴趣点上。他家有个小花园,一直拖延着没改造,横渡大西洋后,他按照在船上的设计思考重新装饰了小花园的地面,再种上一些喜欢的花。
他带着录音笔上船,记录每天的天气、洋流、团队成员的状态、自己的观察、每一次突发事故。一名想当网红的队友几乎没有探险经验,带着不必要的行李,占用狭小船舱的空间,还说只要付了钱就要无限量上网、用电。
刘勇回忆,第一次面对海浪袭来时,这名队友的心率逼近个体极限,海浪不断翻涌,他甚至哭了,需要安慰。刘勇形容他是“探险游客”,冲着网络流量而来,这也是近年来刘勇参与探险时发现的新现象。后来刘勇告诉同事李婷婷,“探险游客”值得研究。
“这些案例都只有他亲身经历后才能发现的。”李婷婷说。
探险的不确定性从组队就开始了。刘勇记得,他去韩国访学时,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帖邀人横渡印度洋,他回复帖子,决定参与。直到上船前,他和队友才第一次见面——全世界拥有跨洋划船经验的约1000人,成功的极少,愿意自己花钱去的更少。当年和刘勇一起横跨大西洋的同伴,大部分人再也不划了。

刘勇和队友划过约8500公里。受访者供图
刘勇曾花30多年在山地探险上,攀登过全球30座以上“未登峰(尚未有人类足迹到达顶峰的山峰)”,探寻并开辟约100条攀爬新线路。
他祖籍山东,7岁时跟着父母到成都生活,对山地环境非常熟悉。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后,他专攻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方向。毕业后,他到四川旅游学院教书,专注山地旅游和探险文化领域的研究。
四川大学校友总会的社交媒体曾讲了这么一个故事:大约是2019年,世界顶级的登山队来四川挑战未登峰,登顶后被告知,那座山峰被一个叫“DA LIU”的中国人爬过了;第二年,这支登山队去苏格兰挑战另一座未登峰,又被“DA LIU”抢了先。
这位“DA LIU”就是刘勇,他的足迹遍布喜马拉雅山脉、喀喇昆仑山脉、横断山脉、阿尔卑斯山脉、落基山脉、南北极……他掌握攀冰、皮划艇、摩托越野、冲浪等技能。因为对山地探险太熟悉,已经“没有未知感”,他决定把探险地转向远洋,尤其是在探险圈公认难度最大、海况最复杂的跨洋划船。
在科研领域,他是四川旅游学院建校以来第一个拿到本学科国家社科基金的教授。王金鹏形容,刘勇性格平静,因为探险时经历的危险时刻太多,生活和工作上的“大事”在他眼里成了都能解决的“小事”。
他的研究生向明霞说,当科研团队进度慢或是学生调研遇到困难时,刘勇总是说,“没事,我来处理”。他的同事李婷婷说,刘勇做的旅游人类学研究,“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。
“全世界范围内,做海洋探险民族志研究的很少,”刘勇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,“学术圈做探险行为研究的也少,许多探险参与者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思维训练,也很难在探险中进行相关学术研究。”
他的录音笔记录着,快到坦桑尼亚时,队友坚持绕行60海里到肯尼亚靠岸,挑战人类最长划行记录,刘勇却认为,抵达坦桑尼亚已经完成首次横跨印度洋探险,且根据海况和气象情况,在坦桑尼亚靠岸更安全。
他尽力说服3名欧洲队友:只要在坦桑尼亚靠岸,就能超越那支比他们提前出发的英国队伍。
在那段录音里,他的队友说,“必须赢”。刘勇说,“我们已经赢了”。
最后,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成了他们这趟探险的终点。4个人花了65天1小时45分,划了约8500公里,突破了多项世界纪录:人类史上首次无动力划船横渡印度洋、以团队形式、划行距离最长、时间最短。快靠岸时,刘勇站在船上,挥起了提前准备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。
不久前的7月31日下午,刘勇站在四川旅游学院的学术报告厅,向听众展示他身上深浅不一的疤痕、正在愈合的伤口,分享他在印度洋上的经历。那天,他已经刮掉了胡须,戴回了眼镜,变回了那位文质彬彬的刘教授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晞来源:中国青年报
2025年08月20日 06版
责任编辑:张毅





 浏览量:
1317
浏览量:
1317 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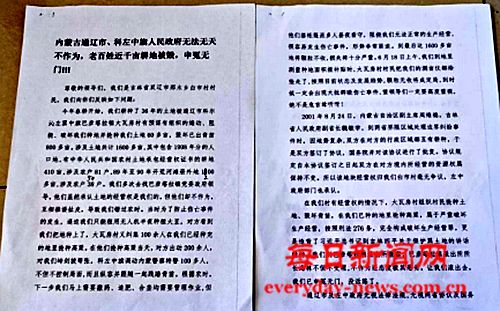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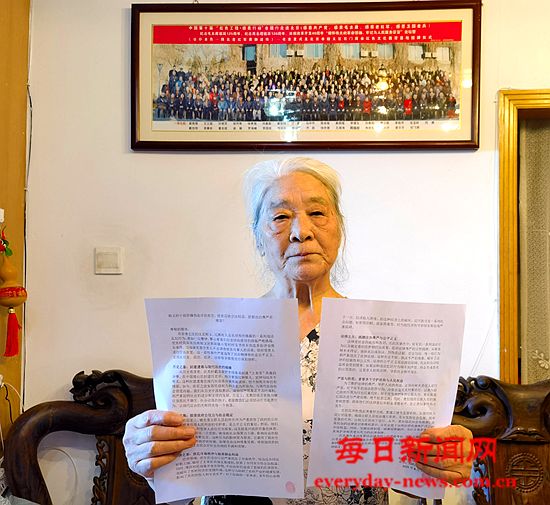



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6001号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:0110537号
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6001号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:0110537号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