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8月15日,深圳的蝉鸣声中,张海涛的家属仍在等待一个答案——原万科轮值总经理、城市更新群负责人张海涛,因“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”被判8年有期徒刑已服刑5年,但围绕“借款”与“受贿”的争议,始终像一团迷雾,笼罩着这场“高管陨落”的悲剧。此前,《红星新闻》报道,张海涛在庭审中称,自己被人构陷。

原万科轮值总经理、城市更新群负责人张海涛
从2014年万科推行“强制跟投”政策开始,一张“借款”的借条,最终演变为刑事判决书上的“受贿”罪名,背后交织着企业制度的压迫、劳资矛盾的激化,以及房企巨头在旧改项目中的灰色操作。这场“罗生门”的真相,远比判决书上的字句更复杂。
强制跟投:高管的“生存压力”与借款的起点
张海涛的“借款”故事,必须从2014年万科推出的“强制跟投”政策说起。根据万科内部规定,公司要求管理人员(尤其是城市更新、项目开发等核心岗位)必须对开发项目进行“强制跟投”——若不参与,将被纳入“黑名单”管理,职业前景直接受阻。
作为万科城市更新群负责人,张海涛被卷入这场“全员跟投”的浪潮中。从2014年到2020年,他参与跟投的项目多达40个,累计投入资金数千万元。“这些钱不是小数目,靠他的年薪根本扛不住。”张海涛家属称,“跟投的钱是他自己找供应商借的,因为公司不允许高管从银行贷款或向外部高息借贷,只能找合作方‘周转’。”
这一说法在张海涛本人的陈述中得到印证。2020年万科审计期间,他在谈话中承认,与供应商郑某、季某、黄某的借款确实用于项目跟投,金额分别为685万元、400万元、200万元。“当时公司逼得紧,不跟投就没项目做,没项目做就没有收入,只能先借钱填坑。”
但这一行为,早已触碰了万科的“廉洁红线”。根据万科内部制度,高管禁止与供应商发生“非经营性资金往来”,否则视为违纪。张海涛的借款,从一开始就被公司视为“违规”,但真正将他推向深渊的,是后续的一系列连锁反应。
举报、降薪与离职:矛盾的激化
2020年上半年,一封匿名举报信打破了张海涛的“平静”。举报内容称,张海涛“在外开设房地产公司”“向供应商大额借款”,涉嫌利益输送。万科迅速启动调查,但最终查明“开设房地产公司”系谣言,借款一事却坐实。
然而,万科的处理方式远超“调查”范畴:张海涛的工资被减半,负责的核心业务被全部收回,最终被“劝离”公司。这一决定,成为他与万科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。
2020年12月,张海涛办理离职手续时,提出了一个“合理”诉求——支付他十多年来累积的年度奖金(税后合计1137万元),以及尚未兑付的项目跟投款。这些奖金自2014年起便委托给万科关联企业“深圳盈安财务顾问企业(有限合伙)”管理,用于购买万科股票,离职时理当返还。
但万科的回应异常强硬:“你向供应商借款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廉洁纪律,甚至涉嫌违法,公司未追究你责任已是开恩,还有什么资格谈条件?”
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张海涛。他当场反驳:“你们的屁股就干净了,一屁股屎不知道臭!”这句激烈的指责,不仅是对万科的控诉,更撕开了一个被掩盖的秘密——万科在旧改项目中的灰色操作。
旧改项目中的“四套房子”:万科的“行贿”与张海涛的“反击”
张海涛口中的“一屁股屎”,直指万科2020年为获取深圳某旧改项目开发权,向相关人员输送巨额利益的隐秘操作。
2020年,万科为拿下深圳某统筹旧改项目,多次与社区负责人洽谈未果。此时,万科集团副总裁、首席财务官、南方区域总裁孙某亲自出马,拜访了原某区区委书记,希望“获得支持”。
谈话中,该区委书记提及:“我朋友名下有两套住房,在你们旧改项目内,还没签拆迁补偿协议。”孙某心领神会,承诺“妥善处理”。
为“让领导满意”,万科煞费苦心编造了一个“四套房子”的谎言:
其朋友实际拥有的两套房屋,被万科以“上调收购价”为名,按17.5万元/平方米(远超当时市场价7.33-8万元/平方米)补偿,合计3220万元;另外虚构的两套“由其朋友指定一个近亲属签订虚假的拆迁补偿协议,补偿2180万元;
四套“房屋”总计补偿5400万元,其中3900万元被指为“行贿款”。
2020年12月9日,在孙某授意下,这笔巨额资金通过关联公司完成支付。张海涛的“反击”,正是源于对这笔“见不得光”操作的知情。他深知,若自己被定罪,万科的这些“秘密”将永远被掩盖;而若他“反抗”,则可能成为万科“弃卒保车”的牺牲品。
从刑拘到8年刑期:借款为何成了“受贿”?
2021年1月13日凌晨,张海涛在睡梦中被深圳经侦警察带走,次日因涉嫌“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”被刑事拘留。
2022年12月15日,深圳市盐田区法院一审以“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”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,并处罚金50万元。法院认定,张海涛“以借为名”收受郑某500万元、季某400万元、黄某200万元,利用职务便利为三人谋取利益。
但张海涛的辩护律师指出,法院的认定存在多重矛盾:
1、借款用途的真实性:张海涛的借款除一笔缴纳学费,两笔用于购房,其余全部用于项目跟投,且有借条、银行流水、《借款费用统计表》等证据证明,属于正常借贷;
2、“谋取利益”的荒诞性:郑某的裕灿公司承揽的旧改项目,实际结算价低于合同价3.3%(1126万→1088万),万科未超额支付工程款;季某的圳通公司、黄某的宏泰达公司均通过万科正常采购流程中标,张海涛未干预任何环节;
3、退赃行为的遗漏:张海涛已于2020年12月全额偿还借款本息(其中本金685万元+利息991208元,总计7841208元),属于“积极弥补损失”,但法院未予从轻处罚。
更关键的是,万科内部暴露的“四套房子”行贿案(3900万元),与张海涛的“借款”形成鲜明对比——若张海涛的借款是“受贿”,那么万科向“刘某某”支付的5400万元又该如何定性?
但法院最终未采纳这些辩护意见。二审及再审申请均被驳回,张海涛的8年刑期就此落定。
当“借款”成为“原罪”,谁来定义“正当”?
张海涛的悲剧,本质是企业制度缺陷、劳资矛盾激化与企业灰色操作的“三重叠加”。强制跟投政策将高管推向“必须借款”的困境,离职时的奖金纠纷暴露了企业的“卸磨杀驴”,而旧改项目中的行贿操作,则撕开了房企巨头“合规”外衣下的暗疮。
在这场“罗生门”中,“借款”与“受贿”的界限被模糊:当员工因企业制度被迫借款,当还款行为被视作“认罪悔罪”,当企业自身的违法行为成为“封口”的筹码,司法判决的公正性,究竟该如何守护?
正如张海涛在庭审中所言:“如果向供应商借钱是罪,那万科的旧改项目又是什么?”目前,张海涛的申诉仍在继续。这场关乎个体命运与企业伦理的案件,或许终将落幕,但它留下的追问,不会停止。
编辑:唐玲





 浏览量:
3728
浏览量:
3728 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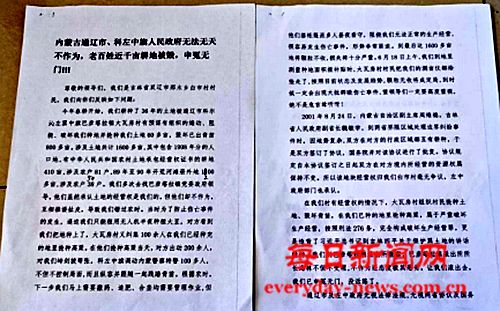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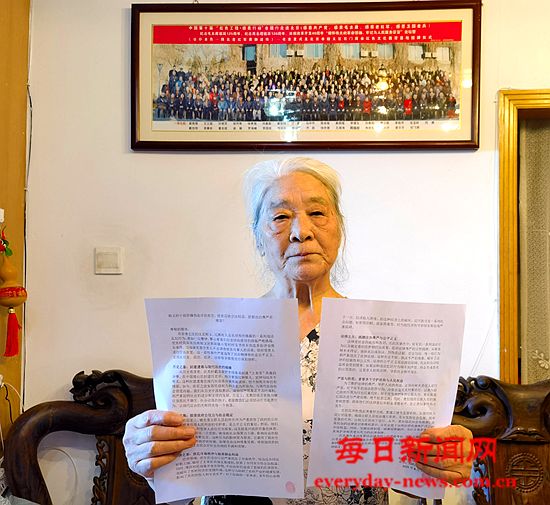



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6001号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:0110537号
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6001号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:0110537号




